时间:2011-03-19 | 来源:傅德锋 | 阅读:1217次
专访于明诠
时间:2008年7月20日
地点:见山见水楼(济南于明诠寓所)
受访人:于明诠(山东省书协副主席、山东艺术学院硕士研究生导师)
采访人:傅德锋(书评家)
傅德锋(以下简称傅):于老师您好!见到您很高兴。首先感谢您接受我的采访。您是我所敬重的一位在全国书坛具有很大影响的书法家,同时也是一位非常优秀的书法理论家和教育家。前一段时间拜读了您的书法理论专著《是与不是之间》,感到里面有很多独到的个人见解,很受启发。这次我到济南来,目的是请教学习,有几个问题提出来,希望得到您的指教。第一个问题,新时期以来盛行的书法展览文化已经经历了轰轰烈烈的27年,我想请您就书法展览文化的利弊得失谈一下自己的看法。
于明诠(以下简称于):我很欢迎你的到来。但首先我得给你纠正一下,你前面给我戴了很多帽子,什么这个家那个家,这都不妥当,我就是一个普通的书法老师,而且是从一个书法业余爱好者刚刚转到一个专业的书法教师的岗位上,并且在书法教学这个领域,我还算个新兵,我这样说,不是客气。你问的这个问题—书法27年来展览文化的利弊得失,我是这样看的:展览这个形式它不仅仅是书法这个艺术门类有的,而是所有的视觉艺术进入现代社会形态以后,它都是以展览的形式出现的。在民国、清代以前,我们国家的视觉艺术就是存在的。你比如说文人画、书法和工艺制作,这些艺术作品完成以后,它们的的成果是如何来推向社会的呢?也就是说通过什么样的方式来得到社会的认可呢?当然它不是通过集中起来展示给社会受众这样一种形式来打通的,它是靠一种特殊的方式,比如说,在一个文人圈子里互相展示品评,比如说把工艺品送给达官贵人,供奉给朝廷,达官贵人再相互之间当作礼品赠送。它是在一个小圈子里面流通从而被社会认可的。而展览这种形式,它在人类社会上出现也不过就是两三百年的时间。在西方,它最早是“沙龙”式的,就是把作品放在一起,大家开个讨论会,一边观摩作品一边讨论,这是最早的展览形式。后来,西方开始有了专门的展览场馆,很多艺术就有了独立的生存空间,这样他跟社会受众交流起来就非常便利。这种形式引到我们国家是民国以后,我们经常看到一些资料,像吴昌硕、齐白石、徐悲鸿在当年曾经举办过展览。但他们那个展览基本上属于沙龙形式,比方说,他们在某一个酒店里面请大家去把作品挂上,然后互相欣赏品评。这种形式下创作的作品还是和挂在书斋、厅堂或者是完全实用的某个生活场所里的作品是完全无二的。今天我们创作的书画作品,它是怎样推向社会被社会大众所接受的呢?它要通过一个中介形式,这个形式就是展览会,他和过去的那种沙龙式的展览会在形式上有很大的不同。它是属于一种专门的展览场馆,像中国美术馆,它里面可以挂上高三四米的作品,而且把几百件作品集中摆放在那里,还配有特殊的灯光照明,整个空间完全是按照艺术品本身所需要的氛围来设计布置的。而今天的视觉艺术(当然包括书画艺术)生存的社会环境和它跟社会的交流方式显然与没有这种交流方式之前的那种交流方式有了一个根本的不同。这实际上也就是视觉艺术完成了现代转型,或者说它必须要经过一个现代转型过程。换句话说,我们今天要创作一件书画作品送给朋友,这当然不用考虑展厅要求,你可以按照自己的书斋厅堂展示的要求完成就可以了。但是如果要作为一个纯粹的艺术作品要拿到展厅里面去展示给社会受众的话,你就必须要按照展览这种形式,按照展览场馆本身的特殊要求去创作。所以说,这不仅是书法面临的一个问题,而是所有的视觉艺术在现代社会里面都要有这么一个转换。
至于你让我评价书法展览经历了这么多年,里面有什么得失的话,我觉得这个问题还是不能笼统地看。因为展览既然是一个必然的趋势,那么我们就不能随意去指责这种形式有什么错误。比如说,今天我们不能指责报刊杂志,不能指责网络把书法艺术变成了什么什么,因为这是一个必然的趋势。有了报刊杂志,有了网络之后,我们写的书法作品,我们写的文章跟观众交流的时候它就发生了一个变化,这种变化形式,你适应也好,你不适应也罢;你喜欢也好,你不喜欢也罢,它都是一个很可观的存在。
因此,我看到很多人抱有这样的观点,说现在书法展览这种形式使得书法艺术变得很浮躁了,变得不像原来的书法了,从而指责展览这种形式。我觉得这只是针对展览当中的一些表面现象来说的。今天的书法艺术的发展趋势和生存状态,它肯定与这个社会的政治的、经济的、文化的,包括建筑的等等社会因素的变化有关。而现代展览的特有形式肯定直接影响着书法艺术,那么它会给书法艺术带来哪些变化呢?变化当然是多方面的,对这些变化我们应该客观而冷静地去看。不是说我不喜欢这种东西,就不允许他出现。这实际上也是不可能的。
自唐代出现了高桌高椅,就使得书法艺术也发生了变化。魏晋的时候,大家都是蹲跪在地上,在类似于我们今天生活当中使用的茶几上面来写字,所以那时候的书法作品基本上都是手札式的,都是很小的。到了唐代,有了这样的高桌高椅之后,书法就变成了这样一种形式。到了明代有了这样的高堂大屋,比如像文征明家的那种房子,就出现了两米多高的大作品,当时叫“壁挂书”,就是我们今天所说的很大的条屏。不仅是写四条屏,甚至写到八条屏、十二条屏、十六条屏。这与整个人们居住的环境、建筑和家俱的变化都有关系。所以,你再不喜欢明代的这种形式,你很希望大家都再回到写魏晋那样的字,是不可能的,毕竟周围的客观环境改变了。那么,今天这种现代化展览场馆的出现,应该是整个人类文明的一大进步,这种东西不管给我们带来哪些变化,这些变化它都是很客观很正常的。在这样的一种情况下,就给今天的书法家的创作提出了特殊的要求。也就是说,现在的书法家面对展览就不能仅仅考虑到挂在自己的书斋或厅堂里是否合适,而是首先要考虑作品在跟社会接触的时候,它是出现在美术场馆、美术展厅的。如何让自己的作品适合在这种特殊场馆被人们所接受,才是我们首先要考虑的问题。
所以,我觉得好像不能单独说展览文化给书法艺术带来的影响是正面还是负面,我不大同意从正面、负面来分析这个问题。展览给我们带来了这样的变化,我们应该充分地认识这种变化。在这种具体的变化当中,我们应该如何适应,让我们的作品尽量符合这种变化的趋势,而不是简单地去指责这种形式是好还是不好。
傅:请谈一下你当年在全国中青展上夺得“三连冠”的感受和一些具体的心得体会。
于:说到“中青展”这个话题,我确实有很多感慨,中青展到2000年为止共举办了八届。当时,大家也都公认中青展和全国展一样,也是全国级别的权威大展。后来,由于种种原因吧,书协方面对这个展览有一些新的看法,而社会上也对这个展览产生了很多的分歧,这个展览呢也被停止了。因此,中青展也就成为了一个过去的历史了。我在当时是这么看中青展的:第一,中青展的参展作者和全国展的参展作者基本上是同一个群体,也就是说,在中青展上参展获奖的作者,一般而言,也是在全国展上的参展获奖作者,都是同一拨人。如果要把他们分成两个类型的话,中青展是把参展人员的年龄规定为60岁以内,60岁以上就谢绝参加了。其实全国展按照自由投稿来说的话,60岁以上的作者自由投稿的情况是很少的,除非是特约。所以我就认为这两个展览的投稿者是同一拨人。要说不同,可能主要在于它的评委组成有所不同。全国展的评委是由中国书协的评审委员会为主体组成的,而中青展的评委,一部分也是由全国展的评委担任,另外一部分是由历年来的大展当中涌现出来的获奖高手和一些在大学里边从事书法教学研究的专家共同组成的。中青展的评委班子相对来说比全国展的评委的年龄结构有一定的年轻化倾向,他们的另一个特点是比较注重学术,像曹宝麟、王镛、黄惇、丛文俊、沃兴华、华人德先生等。这些评委大多是大学里面的教授、博导,他们在书法创作、理论研究与教学方面都有很高的造诣,他们在全国都是得到公认的。因此,中青展的评委可能更为注重展览的学术性。另外,中青展自第六届开始,把“现代书法”纳入进来,中青展一次给人们一个印象,就是创作的艺术观念比较开放,比较包容。如果说不同的话,我觉得就存在以上所讲的这些不同。
近几年有人公开地批评中青展,说中青展“提倡创新”,这似乎还不算批评,他们进一步地说,中青展是“流行书风”的“策源地”,提倡“流行书风”,提倡“丑书”,我觉得这个观点好像有点过分。回想以前,在我的印象当中,每一次中青展举办之前,当时的评委主任、副主任和主要的评委以及有关的媒体都发表大量的文章进行呼吁,要大家不要模仿评委的风格,不要模仿获奖作者的风格。而且展览结束以后,对一些模仿评委和获奖作者的风格甚至获奖作者重复自己原来的风格的现象都从各个角度、各个侧面进行了批评。如果我们去看一下历届中青展作品集的话,我们会发现里面有很多现代书法和一些个性强烈的作品获奖,但同时也有很多写得很传统的作品获奖,并且或一等奖。比如王学岭的小楷、陈仲康的行书,都获得过中青展的一等奖。所以今天有人说中青展是反对传统,只主张创新,我觉得这种说法是有失公允的。现在中青展已经停办,也就已进入了历史,至于它的相关得失,我想就留待后人进行一些客观的评价。我就不再多说什么了。
至于说到我自己在中青展获奖的情况,其实也没有什么太多的要说的话题。1993年,我的作品入展全国第五届中青展,1995年举办第六届全国中青展的时候,我写了一件仿古卷绢本的行草书手卷,获了一等奖,这个结果当时非常出乎我个人的意料,现在来看,那件作品也确实是不成熟,有很多的毛病,那件作品和我后来的书法风格也是很不一样。
当时这件作品在获奖的时候,六届中青展评委会采取了一个评审办法,非常大胆的一项改革:叫“一票定终生”。后来一些人也写文章批评这种办法,说“一票定终生”可能在评审过程当中出现很多弊端。我认为这个问题还是要回到当时去看。当时评委会采取这个办法的出发点是什么呢?是考虑每次在评审作品的时候,有个性的作品,某些评委可能要给一个最高分,但在某些不喜欢这种个性风格的评委那里可能就会得零分。这样的作品往往就没有那些写得中庸一点、稳妥一点、风格古典一点的作品得票高。鉴于这种考虑,当时就让每一位评委按照自己的审美,按照自己的个性充分地去施展自己的评审特点,允许每一位评委在所有的入展作品当中挑出两件作品,三十几位评委从中共挑出六十多件作品作为获奖候选作品。后来有很多人说,这样做,可能评委首先要考虑自己的学生、朋友,会有私心,但是评委会当时有一个规定,就是选出的作品在展览和出作品集的时候,每一件作品都要附上相应的评委的名字,评委选拔的这些作品好与不好,责任由评委自负。假如某个评委选拔的作品很差,是自己的学生或朋友,当展览的时候和作品集发行的时候,就让全国的书法人都知道,是评委的评审眼光有问题,评审的公正性有问题。实际上这样做,就使很多评委一般不会拿自己的名誉开玩笑。所以我觉得不能简单的认为这种做法就会助长一些弊端。而且评委最终选出的获奖候选作品最后是由评委主任和副主任讨论决定每件作品该获什么奖。但评委主任和副主任没有权利从入展作品当中推选获奖候选作品,他们只能从三十几位评委推选的候选作品当中确定相应奖次。奖次确定后还要由全体评委最后进行复核,如有某位评委认为某件作品不应该获得某一奖次,则由该评委另外提议然后由大家共同表决,因此,评委主任和副主任的评审权利也是受到限制和监督的。当时的评委班子在评委们没有任何预料的情况下突然把大家集中起来宣布这么一个评审办法,我觉得这在当时还是很有进步意义的。但我作为一等奖获得者,是得利益者,我说的话,有人可能认为带有个人偏见,但我说的这个情况却的确是当时的实际情况,很多媒体都有着方面的详细报道。
后来,我在第七、第八届全国中青展上也获得了一等奖,但这些作品和我以前作品的风格有很大的不同。大家如果对照一下几次展览的作品集,会看得很清楚。当然,有一些批评中青展的人往往拿着我这个例子说事,说我连续三次获得一等奖,可能背后有什么问题,而且还有一些侮辱我人格的话。对此我也不想在这里展开多说,我只说一句话,我们批评作品也好,批评现象也好,一定要本着客观公正,不能凭着自己的臆想和猜测,随意地去侮辱别人的人格。侮辱谁的人格都是不好的,批评者不能侮辱作者的人格,作者和批评者也不能侮辱评委的人格,评委也不能侮辱作者和批评者的人格,我认为讨论这些问题的时候最好有真凭实据。
傅:请您介绍一下您当时是如何准备参展作品的?准备参展作品应该注意哪些问题?
于:这个问题很不好回答。因为每个人的习惯、想法、做法各有不同,我讲的可能也不具备普遍的指导意义,我就简单地说几句吧。一般而言,参加展览首先要发挥自己的长处,而且要尽可能发挥到淋漓尽致,千万不要拿自己的短处跟人家比。也就是说你擅长什么书体你就写什么书体,你擅长什么样的风格你就写什么样的风格,千万不要盲目“跟风”,要弄清自己的优势和缺点,要做到知己知彼,这是一方面。另一方面,就是书写内容要尽量选一些不是被人们写烂了写俗了的,要写那些不太常见而又很高雅的内容,这种内容还要尽量与自己的书法风格比较协调一致。还有一点就是具体到每一次投稿的时候要考虑到自己的创作和上次参展的作品要有所变化和提高。我在六届中青展的时候,写了一个手卷,过后我很注意报刊对我的批评,别人说我那幅字像吴振立老师的风格,有的说有点像王镛先生的风格,我看到这些说法后,尽管并不十分认可,但觉得这些说法也有一定的道理。所以我在1997年参加第七届中青展的时候,又写了一件册页,还是小字,我努力地改变自己的面貌,把字写得很方,用笔很涩,和六届中青展的那件手卷完全不一样。我当时是想我把这件作品拿出来,让评委看看,让全国的作者们看看。我当时是不敢奢望再次获奖的,更不敢奢望再次获一等奖,只要入展就可以了。当评委和作者们面对我的作品时,他们能给我这样一个说法,说于明诠这一次写的比上一次有进步有改变,有新的想法,我想我的目的和愿望就算达到了。到了第八届的时候,我本来不想投稿了,但当时评委会有一个政策,说每一个作者都要采取积分制,规定入展一次得几分,获奖一次得几分,获一、二、三等奖各得几分,谁先积到15分,谁就可以进入评委库,就有可能当评委。我原打算是不投稿了,准备等自己有了大的改变和提高之后再把作品拿出来。但是看了这个规定以后,我本人也不能免俗,我算了一下自己的分值还是比较高的,我想哪怕再入展一次,多得一点分,我就向着那个评委的目标又前进了一步。呵呵,当时完全出于这种很俗的想法,八届中青展时我又投了稿,结果,居然又一次获了一等奖。
傅:目前,书坛上创新口号愈叫愈响,也有一些人提出了“回归传统”的说法。而继承与创新又是一个老话题,请谈谈你对这个问题的看法。
于:书法界从20世纪80年代到现在,30年了,关于继承与创新这个话题老是扯来扯去地没个完,说明什么呢?说明书法界整体的素质太低,我是这样看的。这个问题在文学界、在美术界、在影视界、在哲学界、在思想界,根本就不是个问题!但在书法界却被大家反复地说,反复地说,还这么有兴趣,所以我觉得我们对这个问题的认识太肤浅。因为继承与创新不是两个问题,而是一个问题,是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如果把继承与创新对立起来,就是大错特错。纵观整个人类文明史,所谓的传统,里面就包括着非常鲜明非常强烈的创新在,任何一个时代、任何一种形式的艺术门类,都没有说,我们创新过了,我们要回去,我们要继承,任何一个历史发展时段都不是这样的。比方说“孔孟之道”,这是大家都认为的最传统的东西了吧?孔子是一个标准的客观唯心主义者,他说:“生死由命,富贵在天”,他讲天,实际上是纯粹的客观唯心主义。而孟子是一个很标准的主观唯心主义者,他讲:“吾心即宇宙,养吾浩然之气”,人人都可以做贡献,这不是典型的主观唯心主义吗?也就是说,这个东西它本来完全是两回事,但正是孟子发展了孔子的思想。到了董仲舒,它又回到客观唯心主义,说:“天不变道亦不变”,他讲了很多汉代人对孔子、孟子思想的理解。这个思想到了宋代程朱理学,又进一步地发展变化,又变成另外一种形式。整个儒家的思想它就是一个不断创新的过程,这也是继承,继承的同时又是创新,创新恰恰体现了他们的一种继承的态度,他们是怎么继承的?他是以创新这样的一种姿态来继承的,这本身一点都没有错。但是今天有一些人非要说:“你们这样是创新的”.我们来看一看书法界,有那一个人是从没临过帖走向书法创作成功的?恐怕没有。他没临过颜真卿,他也许临过柳公权,他可能临米芾少了一点,但他可能临苏东坡多了一点;他可能对明清的书法临得少了一点,但他可能对魏晋的东西学的多了一点,反过来也是同理,这都是很正常的。所以,我们不能从一件书法作品的创作风格、面貌、样式上以为和你所熟悉了解的那种古典风格差别得远了一点,你就认为他是创新,没有继承,不能这样下结论。
胡总书记曾反复讲过,创新是一个优秀民族的灵魂。这个道理讲得是对的,也是很深刻的,这在哲学上具有普遍性。如果说有谁从来不学古人,也从来不看古人的东西,然后写字,完全无中生有地去搞什么创作,那你可以指责他,但是这种情况是很少的甚至是不存在的。再者说,我们继承古人学习古人,我们首先要看一看古人是如何继承他们的古人的?我们要看一看王羲之是怎样继承他的前辈的?再看看张旭、怀素、扬州八怪、刘墉、何绍基、于右任,他们是怎样继承前人的。我们应该从古人的这种学习方法当中来找到一个学习继承古人的正确的方法,而不是凭着自己的好恶把继承古人锁定在几家、几种或者几本字帖上。
傅:当年在书坛上曾有过一场非常激烈的美丑之争,而美丑又是一个相对的概念,互相之间是一种辩证统一的关系。请谈谈您对这一问题的看法。
于:美丑这两个概念在美学意义上跟在生活当中是不能混为一谈的,生活当中有美好的事物,也有丑恶的事物。生活当中的美丑似同冰炭,两者不可调和。而艺术上说到美丑的时候,它的含义是多层次的。有好多人(包括古人、今人,东西方的学者)讨论形成一个共识,就是美和艺术其实是不相关的,艺术的东西并不是以美或不美来判断的,不是说美的东西就是艺术。像我国的美学家高尔泰就有过这方面的论述,例子很多。
艺术是人类精神领域的一种活动,艺术创作他跟每个人的思想感情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每个人的思想感情有都具有个性,有很强烈的个人因素,所以不能一刀切,也不可能有一个标准答案。书法艺术也是如此,我们不能从书法用笔线条、点画的轻重、枯润和结字以及章法构成的形态去表面化地划分美丑。我经常在讲课当中一直坚持这样一个观点:艺术可以分雅和俗,即高雅与低俗、高雅与通俗,我们不能简单地分对与错、美和丑。比如傅山说“宁丑勿媚”,他这里用的这个概念,很显然不是指生活当中人们很讨厌的那种丑恶,如果是那样的话,用到这里肯定是不合适的。那就是生活当中的丑恶比媚俗也好不到哪里去,傅山不可能这样来思考问题。那么他为什么要提出这样一个问题呢?因为他发现,在当时那个时代风气里面,有一种东西是很低俗的,而且甚至是很恶俗的,而这种媚俗和恶俗的倾向是不好的,要矫正这种倾向的话,他就要从相反的角度来倡导,也就是说,宁愿把字写得朴拙一点、丑拙一点,从而来达到自己主张的目的。所谓矫枉过正,傅山不可能拿一个同等于低俗或者很恶俗的档次很低的概念来反对当时的那种不良风气。所以我觉得现代人老是习惯于从美丑的角度来谈这个问题就未免简单化了,或者说从潜意识当中没有把艺术上的美丑与生活当中的美丑区分开来。
傅:您觉得书坛上存在所谓的“丑书”吗?
于:如果把它(丑书)完全当作一个贬义词来理解,就是当作一种很不好的书法来理解,丑书当然是存在的。任何时代都是存在很好的书法,也存在大量很不好的书法。或者说存在一些根本就不能称之为书法的那些书写遗迹,对吧?如果你把这个东西叫做丑书、俗书、很坏的书法或叫做远远够不上档次的书法都是可以的。但是作为我们的理论家和作者,本不应该关注这些东西,只关注好的东西就可以了。这些不好的东西,从创作的角度而言根本不值得我们去关注。但是从社会学的角度也无可厚非,因为我们既可以研究学雷锋,也可以研究反腐败,这是另外一层意义。为了推动艺术的发展,我们也可以去批评那些不良现象,但是我们主要地是认准哪些是好的就可以了。然而,今天人们在谈论丑书这个问题的时候,往往里面掺杂了很多非艺术的因素,他们往往指责一部分人、一部分作品,这个问题就不是这么简单了。我举个例子:在《中国书法网》和《书法江湖网》以及很多网站上有一个帖子非常火,火了几年了,说王镛、沃兴华、白砥、于明诠他们都是非常浅薄的,然后就把我们批得狗血淋头,说我们写的简直是胡闹、丑恶至极,甚至说我们是狗屎一堆,这些话呢其实都是一些侮辱性的语言,在网络上散布,我们也没办法去计较了。后来又有一个帖子,说我们四个其实是很高明的,从反意义又把我们狠批了一通。我打个比喻:就像煎鱼一样,把我们这一面煎糊了以后再反过来煎另一面,反正是要把我们“赶尽杀绝”。我觉得,如果把我于明诠的字骂得狗血喷头,是“狗屎一堆”,我没什么意见,我写的本来也不好,我从来也没有觉得自己写的有多么好过。但是我在想,其他三位先生的字,大家还是要客观地来看。比如说王镛先生,他在20世纪80年代中期的时候,已经在全国书坛得到了大家的一致认可,确立了自己的地位。他的作品是好是坏,人们已经给了一个公正客观的评价。可是经过了20多年的发展,反而把王镛先生说得一无是处,这里面有一些很值得反思的问题。我们虽不能说王镛先生达到了多么高的高度,但我们起码不能说他是胡闹或不会写字。如果从这个角度来认识王镛先生的话,这里面肯定有很多艺术之外的因素,这只能说明当代书坛很可悲。再比如说白砥,他年龄虽然不大,但他的临摹功夫我认为在当今书坛绝对是一流的。包括沃兴华先生,大家看看他与白砥先生的临帖和他们谈临帖以及创作的体会文章,你就会发现,第一,他们有深厚的传统功底;第二,他们有深刻的思考;第三,他们的创作很有思想深度。我们不能简单地以自己看不懂或者看不懂就说他们是瞎胡闹。这样来说话,是不负责任的。当然,你非要这么认为也没有办法,如果很多人这么认为,或者有一部人总是以这种话题无理取闹的话,那只能是我们整个时代的悲哀。说明人性背后有很多卑鄙龌龊的东西在里面。
傅:本来流行书风作为新时期书法发展历程当中的一种特殊现象,它本身可能存在一些这样那样的问题,但他的积极意义也是显而易见的,可在很多人的认识当中却成了一种近乎贬义的东西,您是如何看待这一问题的?
于:这个问题回答起来就比较麻烦,我只说这么几点意思吧,“流行书风”这个说法,是20世纪80年代中期出现在书法界的,最早是《书法》、《书法报》发表的一些文章里面出现了这个词。这个说法在书法界被大家反复地说了20多年,在这20多年当中,很多人指责自己不喜欢的、很反感的一些不良书法现象,但大家指责流行书风现象又各不一样,而是每个人心中各有不同的指向,有的人说这样一种风格是流行书风,有的人说那样一种风格是流行书风,并不是一个大家都认可的完全统一的现象叫流行书风。有很多现在已成名的代表性书家,当年都曾经被指责为他们的作品是流行书风。不仅今天参加“流行书风展”的作者,有很多反对“流行书风展”的名家、大腕当年也曾被指责为是流行书风,大家只要翻翻以往的报刊杂志就会知道,这是一点。第二点,既然这个说法在书法界闪闪烁烁、隐隐约约,有时小量、有时低回,被大家说了许多年,那么,为什么到了2000年以后,反对流行书风的呼声突然之间大面积地爆发,围剿流行书风成了一道风景了呢?这里面有很多令人深思的地方,这里面有很多体制、权势或某个掌握权势的人的观点以及很多甘愿充当体制、权势和某个权势人物的棍棒、打手等等的因素。有很多人反对流行书风,批评流行书风,把矛头指向某某某、某某某,其实他们不过是表现给当时掌握书法界权势的某些人物和书法机构看的,就像“文革”时期一样,他是带有“站队”性质的。我们从历年来批评流行书风的很多文章里面可以看出这一点。这说明什么呢?这说明书法界“文革”的遗风依然存在,这种倾向很可怕。它不在于批评了什么,也不在于它批评得怎么样,但以非学术的因素来理解学术问题,这是非常可怕的一个倒退。“兰亭论辩”刚刚过去才几十年,启功先生曾经为自己几十年前在那场论辩当中犯的错误一直追悔莫及。而高二适如何在当时那种政治高压的情况下坚持了自己的观点,这些故事这些人物,我们不应该这么健忘。第三点,流行书风展举办的时候,曾经有人问,你们解释一下,到底什么是“流行书风”?当时主持人让我来回答这个问题。我当时指着流行书风展展厅立面的所有作品说:“这就是流行书风!”也就是所有参加流行书风展的这些作品就是流行书风。而所有的关于流行书风的批评都应当集中到这些作品上,应该就这些作品的得失成败来谈你的学术批评观点。但是,我们当时举行的“流行书风论辩会”上,邀请的很多理论作者,他们的批评“流行书风”的文章,很少有从学术方面提供一些有价值的观点的。大多数都是从一些非艺术因素、一些现象或者自己拟定一个靶子,猛攻猛打,而对“流行书风展”的作品视而不见。所以石开先生说:“你们批评流行书风的这些文章作者,我觉得你们缺乏起码的看图说话的能力。”我认为石开先生的话说到点子上了。第四点,关于流行书风这个词到底怎样来理解,今天很多人说,你们不应该用这个名称,这个名称不好,这个词很容易被人产生误解,而整个中外艺术史告诉我们,很多的流派、风格和一些以书法展当中的阶段性创作倾向都是在大家的不理解、讽刺、谩骂当中形成的。比方说西方绘画的“印象派”、“现实主义”、“野兽派”都属于这种情况。像流行歌曲、朦胧诗当初也不是褒义词,再比如上世纪三四十年代赵树理的小说被称之为“山药蛋派”也不是褒义词。像“鸳鸯蝴蝶派”等等,这些当初都是被人们嘲讽和批评的一个说法,这种说法后来就成为了一个符号,这个符号它有特指。如果有人说:“山药蛋派是什么呢?”我们就可以很直接地回答:“就是赵树理那样的小说风格,”对吧?至于说“山药蛋派”好不好呢?那你要看赵树理的小说好不好。一句话概括,就是不管你批评“山药蛋派”还是“野兽派”,你不能仅仅针对这个符号本身,你只有针对这些具体的作品展开批评才具有积极意义。批评流行书风也是如此,你不能只针对流行书风这个词,要从具体的作品去分析,如果这样的话,这种批评自然是值得肯定的。在这种情况下,你无论把流行书风批评得再怎么体无完肤,我认为对流行书风作者,对整个书法艺术的发展都是有历史功绩的。但是,如果通过打击、谩骂等等手段来达到他们不可告人的目的的话,是十分浅薄的,甚至是卑鄙无耻的。
傅:书法批评在当代一度不景气,而在很多人看来,从事书法批评就是选择了一件得罪人的事。但是,一些有志于书法批评的人士又不愿意放弃自己在这一方面的追求,可他们在现实当中又会遭遇很多尴尬和无奈,请问,您是如何看待这一问题的?
于:关于书法批评,大家都有一个共识,即当代书法批评缺席。书法批评在进入现代社会完成的转型比较缓慢。像美术批评、文学批评都比较独立。本来批评与创作是一对孪生兄弟,现代艺术离开现代批评简直无法生存,艺术创作如果离开批评,将会很不正常。因此,我们非常希望能够看到公允客观的书法批评。如果你是一个很负责任的批评者,你就应当用良知和思想水平说话。而那种不着边际的、不负责任的信口开河式的所谓批评是根本不利于艺术的正常发展的。而正常的批评应该关注书法文本,尽量避免非艺术因素的干扰。但由于中国根深蒂固的陈旧思想,比如官本位思想就直接影响着书法批评的正常进行。总之,书法批评难度很大,短时期内不会有太大的改变。良好的书法批评社会氛围的形成还有待来日。
傅:目前,我感到书法理论界有一种不良倾向,很多文章从所谓学术规范的角度来看无可指责,但就是文章写得晦涩艰深,古奥难懂,让大批的读者望而却步,敬而远之,而我们写文章的目的是准确明白地向读者传递自己的思想观点。你对这一现象有何看法?
于:这个问题我觉得是这样,由于每个人所读的书不大一样,有的侧重东方的,有的侧重西方的。有人写理论可能西方式理论用的多一些,但也没有什么可怕。关键是我们不要故作高深,在讲究学术规范的时候还要尽量注意让自己的文章通俗一些,好让更多的读者所理解和接受。
傅:鉴于时间关系,您工作也很忙,这次访谈就到此为止吧!您讲的很精彩也很深刻,这些将会对广大书法人有一定的启发。还有很多问题,以后有机会再请教。再次感谢您!
(根据录音整理,未经本人审阅。有出入之处敬请于明诠先生谅解!)



 保存
保存 打印
打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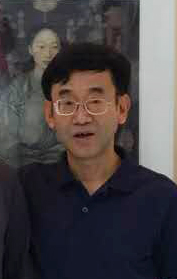
最新评论
已有0条评论,共0人参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