旋转于城市的喧嚣中:世俗的色相
时间:2008-11-25 | 来源:白采水 |
——序赵夜白诗集《城市化石》
网络化以及由此展开的虚拟世界以另一种颇有点反传统的意味但却来得更活跃的方式在人类日常生活中早已确立,并且介入甚至直接参与人们的各种社会活动,其便捷性与广普性似乎为早陷入尴尬境地的文学带来一个新的转折的良好契机;而事实上,网络文学的兴起和广大文学爱好者(很多还是网络文学的直接参与者)阵容的日益壮大,的确为当代的文学带来了表面上的繁荣。然而——不妨举个例子——正如上个世纪末各种诗歌流派层出不穷,但建立于吵吵闹闹之上的虚幻大于实际的浮华并不能掩盖其内在的无序与苍白。兴许这就是一路上攻城掠阵的现代物质文明与相对滞后的精神文明因不相吻合而生的冲突所需付出的代价,并且得由这一切的缔造者与促成者——人类——悲哀地承担着。但不管怎么说,现今的文学就是这般存在着。
我们再特别地说到诗歌。作为一位诗人,其实我更愿意以评论家的身份(欣赏者也无妨)出现。如此这般,我便可以较为客观地、冷静地审视自我以及现存于诗坛上的各种现象并作出同样较为客观与冷静的恰乎理智的分析。但在另一方面,则因带着批评家的高姿态,我难免对诗人和他的作品的要求显得近乎于苛刻。然而我认为这是合理的——在坚持文艺本身的运行规律的前提下。因为只有经得起推敲的诗歌,才可能表现出某种程度上的生命力。历史事实也证明,一个时代的诗歌(文学)总体成绩如何固然得由与该时代相对应的诗人们成全,但评论者的作为亦起到推波助澜的作用——无论是予以促进还是予以阻滞;甚至可以说,一个诗歌没落的时代,坏就坏在评论者玩闹中的捧杀或违心的贬责。我们的教训是很明白的。
无论是诗人自身还是一般的诗歌欣赏者,对于诗歌本体,都会有自己独到的看法——不论是否成体系,也不论合理性与科学性有多高。我想我的朋友——本诗集的作者夜白先生——亦一样。这在他的诗歌里有诸多反映。然而请容许补充一点:我同夜白并不算熟识,仅仅读过他的简介和这本集子方有些许了解,但这是好事,我遂可以免受情感的左右而陷入先入为主的感性的误区,这也是我一口应承作此序言的来由;相反,如果是我身边的老朋友,我则要谨慎考虑了。而另一个本质的因素是,我一直以为人类最真实也最伟大的情感是隐秘着的,内敛而不外露,即便在平常琐碎的生活中人的行为举止多少能够透露心灵的信息,但那是多变的、不稳定的。而对于诗人而言,能确切地代表其精神实质与人格力量的惟有他苦心完成的诗歌以及煞费心力营造的诗歌境界。诗歌的永恒魅力也正在于此间。在相形下要来得琐屑的物质生命世界里,人类很多美好的情感注定是无法满足的——人的一生何其短暂,并且消弭于琐碎与世俗的生活中——而在这个程度上诗歌或许可以略略地弥补人类精神世界的空白与缺憾。所以我对于诗歌——也仅仅是诗歌——除了为文者应有的热诚外还有一份格外的虔诚;而我所能给予我的朋友夜白的也就只有这份热诚与虔诚。
诚然,在长期的艺术实践过程中,夜白不仅积累了他的经验,亦有他自己的所得,他的诗歌里所吐露的文艺观点亦清晰。在浓郁的传统文化的家庭的熏陶下长大并以颇有成就的画家姿态出现的夜白,其文学造诣自不容轻视。文艺是相通的。画家对于光线和色彩的敏感和迅捷的捕捉力运用于诗歌以及诗歌创作的实践上终究表现出极大的活力,灵感找到正确的切入口则势必得以恰如其分的宣泄——
我是这冥冥的泪滴
因为你悲伤而出世
在这淤积的哀怨里
凝成这如水的冰晶
——《过客》
发自于心灵至深处近乎失语的梦呓般的言语却得以如此从容地抒就,其顺畅的文思以及不可多得的抒情才赋,在此可见一斑。然而一个稍有作为的诗人,他的眼界自然不会放得这么低——仅仅局限于个人的情感而徘徊于自我狭小的抒情空间——而必然投诸于更为广阔的社会生活。夜白作为一个颇为自觉的诗人,他做到了这一点。城市生活所能给予他的切肤感触,在他诗歌中洋溢、明白无误地打颤;情绪的波折,予以形象化的演绎,无论是深沉还是轻巧,无论是宣泄其淡淡的哀愁还是泯之于一笑,都表现得无限真挚,真正做到“晓人以理,动人以情”。以城市人的眼光看待城市以及同城市相关的层层面面,颇有可取之处,其最大的优势便显而易见了,即表达自己熟悉的生活经历,这一方面易于材料的积累和情感的从容自如地抒发,这样也就更能够打动读者的心、引发各个层次面的读者的共鸣,而另一方面则成就了他的诗歌本身,如厚实度,如含金量——尽管城市问题已有不少作家探索过,并取得了一定的文字上的创作实绩。他把诗集命名为“城市化石”,我猜想,他隐约有这方面的含义。
于是我们自然又说到城市。其实对于城市这个概念,我们是再熟悉不过的,尤其是现代化和城市化进程的加速推进。然而在拥挤的街道、喧嚣的人群之外——深藏于日常生活琐屑的表面之下的更深层次的诸如文化和人类终极关怀等我以为要来得更纯粹些的精神实质,我们究竟懂得多少?且先看诗人眼中的城市:
不知道街道上人在忙些什么,
不理解路旁乞者的悲哀。
不知途经城市天空的群鸟,
向着哪个方向徙飞。
——《城市疑惑》
物质生活的高度膨胀而精神世界相应地收缩,使得连同文化人在内的世人日益功利化——这已是不争的事实。是的,文化的转型(主要是向商业化靠拢)在上个世纪末就已大刀阔斧地开展,发现到如今更是一日千里。而另一个事实就是,外在生存环境的艰难,必然又加速了文学者群体的分流。对于此,我们不必过多地指责旁人——尤其是那些曾经是文学上的中坚力量者——弃文学(或这边所特别提出的诗歌)而去,但有一点是毫无疑问的,我们理所当然要尊敬那些坚守文学阵线的广大诗人作家们。
但必须指出的是——这就回到开篇初所谓“网络文学”的现状问题——这种文化的转型,难免促成文学审美情趣的裂变,人们审美方式的改变,又难免不在作家们的创作上留下或深或浅的痕迹。如今网络上各种文学流派走马观花似地流转与变更即是明证。口号大过于创作实绩,便表露出浮华与空洞背后的虚幻。以诗歌创作为例,无论是意识流还是写实派、无论是口语派还是学院派、无论是身体写作还是垃圾派——如若说其理论还有一定可取之处并表现出一定的合理性,那么其创作则显得幼稚可笑。关于这点,其实历来都如此——即便是历史上那些曾掀起过蔚为壮观的洪波的诗歌派别,几乎无一例外。这值得我们深思。
在网络中厮混(但我想骨子里他决不把自己当网络诗人看,他更是严谨的艺术家),但夜白竟然好象全然不为时兴的诗歌创作所动似的——至少说他所受的影响小些。须特别强调一点,正如上边所说,我仅仅关注诗歌本身,在此我不带任何情绪,我无意于轻视网络诗歌,更无意于贬低任何一种诗歌流派。是的,我只针对于我的朋友夜白的诗歌。怀着敏锐的眼光的诗人对诗歌进行自觉地创作,无疑保留有他独特的见地和才思以及行文规律,诗人个性化、典型化的为文的作风表现在诗歌创作的实绩上,就好比一股清新的空气吹入众人心田,不但不陷入俗套,还甚能醒人、怡人;当然这只是其一,而其二是下文所要说的,敏感性好、穿透力强的诗人,总不会满足于既得,而必然不惮并不倦于对诗歌作多层面的探索——微微遗憾的是,这点夜白似乎做得不够。
总得说来,夜白的诗歌,无论在抒情方式上还是题材的取舍上都是较为传统的。这并非是坏事,倘认识到位甚至还有这点好处:取那些用得几近烂熟的话题,即在寻常的生活中翻新、获取新的独到的灵感,必然对创作者提出新的更高的要求,而对于有所作为的诗人来说,必然刺激他把眼光投入生活的至深点,甚至促成他直接参与社会实践,从而达到某种回升。但他眼界有所拓宽,这更是好事一件。不可否认的是,很多日常生活中的尤其是来得琐碎的话题至今还有诗人不屑为之,如城市流浪者、体力劳动者、废物、煤渣,或者动物与人类的生活污水——当然那些演绎得过火的也因此而变得庸俗与狭窄化了的垃圾派诗人们往往对此表现出极大的热诚,这自当别论——甚至是早已融入人类生活方方面面的现代工业如钢铁、路轨等问题;诗路不甚开阔、思想同现今生活脱节,其诗歌定然缺少一份时代的气息。文化——正如人类社会中所有的意识形态——最能表现其优越性方面的特点就是其传承性以及在此基础上的突破与升腾,从而把人类文明推向前进、并上升到另一个高度上。而诗歌最大的特征就是集中地快速地反映现实生活——其便利性同短篇小说有些类似;倘若诗歌同时代脱节,必定缺乏新意,不单容易陷于前辈们苦心经营却成为后人的牢笼的沉重的阴影中而无法自拔,也难以达到现今的审美标准,其存在的意义或价值就大大折扣,创作业绩亦可想而知。这点很多人持不同观点,尤其是那些把诗歌当作纯粹抒发个人情感的自语式的诗人们(与相关的评论家)。当然有些理智些的从诗歌审美的形象艺术本身的规律上特别强调抒情主体的重要性以及直觉等在抒情上的优势与分量,这自然会有合理的一面。但我无意陷于诗歌本体,即文本之争,我只赞成我所以为的更合理的理论样式,那就是诗歌的社会性,因为生活是宽广的、充满了包容性,如若社会意义匮乏——倘若尖锐化地说,如果诗歌不贴近辅之于精神世界的探索等活动在内的以人类生产实践为主体的人类生活,人类审美的本质力量无法在具体并在具体中抽离出来的形象化的语言艺术中得以张扬,则无所谓诗歌这种文体与否了,我们固守的也无外是脱离了内涵与意蕴的诗歌的外壳。
在这点上,夜白则要来得平和些、大度些。世俗的万千色相,几乎没有什么不可入其诗,而他总也努力把诗意拓展到生活的各个角落。他写司机、写浪人、写乞丐、写政客、也写落泊的艺术家;他写公路、写广告牌、写监狱、写酒馆、写街灯、也写垃圾;而他游离出平常生活中的人、物及社会事件之外的人类的各种情感则更是饱满、丰腴、富有感召力。“你的眸子定格为雪 / 又不忍烦乱春天的美丽”、“如今鸟雀已带不起我的步子 / 田地中也少了一份宁静”、“我本说是找到一个 / 终身不必更换的巢穴 / 用终身的血泪积攒 / 在里边含化珍珠”,此等感人至深的诗句俯仰皆是。对于现代都市以及都市中的人们的生存现状和情感世界的探询,夜白的感触不可谓不深、思想感情不可谓不真。以下就对作者诗歌中表露的所指做初步探索。
孤独是人类恒久的话题,夜白也不能免俗。“我们在竹林里寻找 / 像尾泥潭里缺水的鱼”,现代生活日趋平常甚至平庸化,对稍有自省者来说都是一种莫大的痛苦。人都有向善、向崇高的一面,我以为这是人类诸多美好情感的来由并把这些情感发挥到极致——人终究有别于动物。旋转于城市的喧嚣中,内在精神的需求并需求得到满足,而外在生存的困境则一再破碎我们(诗人)美好的梦想,甚至动摇我们心灵深处的信念,这不足于引起人心的恐慌么?“蝇营狗苟辘轳般的生活 / 拖着鬼气的屋子成长”,平衡的心态被破坏,甚至再也找不到出路,在狂乱的自语中诗人似乎失去理智了。然而造成这一场蜕变的直接缘由是什么呢?是城市的隔膜,是城市繁荣与拥挤背后更深的空虚。“我满眼装满迷离 / 溢出一种物质”,诗人莫可名状的压抑着的孤独以及因孤独而生就的迷惘便一触即发。可能同夜白的身份有关,他对艺术的近似于崇拜的心理以及因此而发的宁愿为艺术献身的品格,自然令得他不自主地恪守作为艺术家的恬淡而少喧腾的、纯洁而去虚伪的秉性,而环绕着我们的当代生活是何种生活样式?于是我们不难理解,诗人因与城市以及同城市相关的现代生活不合拍而表现了相当程度的恐惧感。他诗歌中的尘世里的种种色相,都是有所意会的,有着深沉的含义。从这点看,夜白把视野投放到日常生活中并且毫不避讳日常生活中琐碎平常的话题并不是自觉的,是在内外强烈的对比冲突中表现出的一种辛酸的无奈,是为了表达他的思想而服务的。在绘画与诗歌中,他都一再流露自身与荷花的多番情结,而在我看来,荷花在诗人生命世界里就是象征着因无人相闻、相识、相和而发的英雄式的寂寞。“天池的荷花 / 那是我隔宿的快乐”、“相思是一朵过季的荷 / 不幸生在寂静的池塘”,梦醒梦却成空,此种忧郁怎么不叫人喟叹千万?
然而夜白总归要来得恬淡些的,无论是情感的抒发还是遣词用句都来得舒缓。“我愿意定格于微笑 / 忘却一切人为的忧愁”,这或许同他的成长经历有关,他所不曾泯灭的人类宽博的爱和他那崇高的人文关怀让他站得高些、也表现得宽容些,从而有意无意压制着自我感情的外露。确实如此,表现在他诗歌中饱满而诚恳的情绪波动总是这般淡淡地倾诉,诗人似乎以事不关己的架势游离于人群之外,但是呀,拳拳关切之意就藏在每一个诗句中了。是的,世俗的色相,就悉数显现在他淡然的诗章中了。这一方面我要说的是,夜白的诗歌不但以孤独为基调,且充满着爱的芬芳。这是怎样一颗尘世里的心?但两者并不悖离。我有一个看法,那就是夜白所有忧伤与寂寞的来由,全因为他丰富而善感的赤诚之心在平庸化了的客观世界中无法得以展现和满足——他有着怎样一颗尘世里的心?而另一方面,则自然地转入对他诗歌创作技巧方面的探究。
诗歌的情感在于适当地约束而不在放纵,尤其是诗意泛滥之时,否则容易坏了整体美和总体的感染力度。夜白尽可能把内心的感情藏于文字的背面,我深以为之,其感召力甚是明显。诗人在诗歌艺术上的实践,不但在于寻找属于自己的并且稳定的表达方式,还在于确立适合于自我抒情的途径——但这并不是固定的一成不变的,相反可以是多方位的;诗人们的抒情成效的高低差别就反映于此间了。夜白的诗篇写得平实、好读,有点平民化,没有刻意地惨淡地经营的嫌疑,这与他的创作才华和创作方式相称,如
走吧,走吧。
想走多远就走多远,
在没人认识的土地上:
默念伊的名字。
——《浪迹诗人》
他的抒情气质一目了然了。但他难有纵横家的风度,诗艺相对地狭小而缺乏开放者广收博纳的优良作风,使得其风格——或许因已形成固定模式的缘故——缺少变化,这不能不说是一种缺憾。
夜白的艺术表现手法趋于单一化,且不很娴熟。尽管他也有意加强他诗歌内在的旋律以及词语的跳跃性与伸缩性,但他做得不够——甚至可以说他恰恰就生疏于此了。词语的弹跳性与跃迁性不够,诗歌常有的表现方式因得不到较好的舒展而不甚到位,以至于诗歌张力与附着力的普遍欠缺,一方面有损于诗歌作为形象化了的艺术的本质魅力,另一方面则难免影响到(这是一种束缚性的绳索)诗人情感的表达,很多内心的实质不能得到恰如其分的展示。更进一步地揭示,其实上边两方面还是互为因果的,后者可以是成就前者的一个因素、并伙同其他的关于诗歌内外在的工夫的匮乏的相互作用下使诗歌的本质魅力受损。当然我们似乎也不必过多地指责诗人的缺陷,谁都有自己的也只适合于自己的抒情样式,况且他急于出这本集子,也许是其中的一个原因。从他所署的时间来看,百来首诗歌都是本年度整理出来的——不外乎大半年耳——时间的确短促了点,尤其是最末部分显得粗糙了好些。但对于态度真正严谨的诗人而言是很不应该如此草率的。
“工夫在诗外”,诚然,正如上文所说,诗歌艺术在于不惮、不倦的探索,才可能达到自我完善的美好的终极的目的。优秀的诗歌——对于每一首诗歌,尽管我们不能笼统地冠之于“好”或者“坏”,但其间能够沉淀多少有价值的东西方家一眼即可看穿——向来是思想与艺术的完美统一。夜白的诗歌就缺少这么一种探索的先锋意识(这兴许就是夜白艺术表现手法单一化以及因此而生的陌生化与生疏化的重要原因了),“我该向读者忏悔的 / 没能让所有人因诗 / 而幸福而快乐”,尽管他也有向上攀爬的内在要求,以期把更美更圆熟也更有感染力的诗歌奉献给广大读者。但做得不够却是既在的事实。不过关于这点我宁愿宽容些,即我希望夜白有这种探索的意识,只不过还在赶路的过程中,尚未形成规模,诗歌创作上亦未找到适宜的切入口。当然,这就是广泛存在于大千世界中的矛盾问题了。是的,理论价值总不等同于创作成绩,人的愿望也不总都能实现,生活合理的一面同这种合理性背后的悖谬,总是连在一道的。然而我们就听之任之而一筹莫展了么?自然不是的,我们人类的意识是能动的,那就是我们总是寻找着一条或者多条无往而便利的捷径,让矛盾往好的方面逆转,从而解决我们所碰到的难题——人类的伟大之处的确是那些消极承受的动物们所无法比拟的。
或许缘于其平淡的抒情方式的要求,夜白的诗歌表现出程度不一的散化的趋势,如同流水的倾泻自然顺畅却难以收拾与约束。现代生活的琐碎化引发诗歌的解体与重构,为表现与日常生活相对应的主题而适当地散化是可取的,但这有一个度。历史上也有不少方家探索并实践过——如美国的惠特曼和印度的泰戈尔,甚至是上个世纪我国民主革命上升时期的一些诗人——也取得了一定的成绩,但这是同他们特定的时代想应和的,而且那些做得好些的方家们还考虑到诗歌本身的内在要求,而非爽性泼墨一般地快意为之。夜白的诗歌,总体上都是自由体诗,留下了前人探索中的诸多痕迹,在诗意的凝聚、内敛与外收、典型化的把握上是失之于不足的——这毋庸忌讳。但从另一个角度上说,我们都是在前进中的,诗歌是一个不断回升的过程,今日的不足可能就是促成自我完善和沉淀的转折点,在艺术这条无终止的道路上,谁都不可能一蹴而就,谁也不能说他上升到了艺术上的制高点。
倘若在夜白的诗歌整体上、综合夜白创作技巧和固有的思想性、情感性,即总体的文学艺术价值方面作进一步的研讨,则不但可以把上边关于夜白在创作上所表现的各种现象和问题都串成一条线,还能在高处上把握夜白创作的总体特色及创作中可能出现的难题。承上所述,夜白的诗歌居多为自由体诗,即不讲求辞藻与音韵,而以情感(甚至还可能是狭隘化了的灵感)的勃发为凭借注重诗意的渲染和铺陈,这很好地反映出夜白在创作过程中的基本情形。按理说夜白对他的生活和他生活的城市有一定的甚至是切肤的了解,他理当明智些地以更可靠的方式——诗意的挖掘、捕捉与抒发——完成他的创作,然而有意无意过多地依赖瞬息的灵感取胜,颇有点类似于偏走险锋、刀口觅胜,这样夜白无疑不自主地为自己设计好了圈套,因为灵感是不很可靠的,有其偶发性与不稳定性。这又同上边所指的相关夜白处理他生活取材与艺术题材的问题相互合拍了。上文所说 “夜白把视野投放到日常生活中并且毫不避讳日常生活中琐碎平常的话题并不是自觉的,是在内外强烈的对比冲突中表现出的一种辛酸的无奈,是为了表达他的思想而服务的。”这一方面可以说明其作品有一定感染力,即在近似于压迫中所作的反抗并因反抗无力而在情难自禁中自然逸出的呻吟一般的话语,这是真诚的,并能惹人同情,引起普遍的共鸣;另一方面则因夜白的不自觉性,又难免损坏了艺术形象。分析他的作品:如若情与景能够较好地嵌合、意与境的和谐统一能够找到适宜的切入点,则夜白此阶段的创作成绩是可喜的,表现出一定的生机与活力,即得以较完好的演绎;反之则很可能就是败笔。这一方面就是夜白在创作过程中的基本情形了——艰难性,每走一步都充满了挑战、矛盾和危机意识,而另一方面则可以解释夜白总体成就不高的事实。
说到这,一个顶有趣的现象凸现出水面了。承上文所言我以为夜白是少(请注意这个“少”字)受时兴的各种熙熙攘攘的诗歌流派和与之相对应的创作取舍的影响的,但另一个事实的真相是,在字里行句间,夜白的诗歌亦都不同程度地表现出与现今各种审美情趣相似的某种发展趋势。这自相矛盾了么?我认为没有,我也相信我的审美直觉和文艺判断力!其一,我说过我只是针对诗歌本身而言的。对诗歌的抒情主体作必要的了解是必须的,但不是主要方面,更不是理论评说家的本质任务;批评家为了论证与据理的全面性、以免有所纰漏而伤及整体、进而影响到文本的科学性与严谨性,方以辅助的手段去认识抒情主体,即我们的诗人们。而我想我的认识已经到位了,这就够了。况且我还说过,为了少受先入为主的感性认识的误导,我相反还有意识地淡漠(再请注意这“淡漠”而不是一概抹杀)了对抒情主体的诗歌之外的了解。其一,也是更为重要的,我更加情愿相信,夜白在他创作上表现的审美趣味是与当代诗歌中某种意识规范遥相呼应的,是以自省、自觉的方式融入诗歌的大圈子的而非有意模仿而达到这种嬗变。是的,这充分显现出诗人主动地进行诗歌创作的良好的为文态度,更体现了诗歌作为特殊的意识形态的一面:(一)诗歌作为上层建筑的有机构成因素,不能不受该时代的经济模式的影响——即诗歌大潮流总要同现今的生产力的发展保持大体一致的步伐——而这种影响还是起着决定性意义的。一个有所染指的诗人在这方面完全应该是自觉的,时代与诗歌本身对诗人双重的选择必然同诗人自我对诗歌的选择相合拍,表现的形式就是以作品为中介,广大读者对他创作业绩所持的或肯定或否定的态度。所以在这个意义上说——我想事实也应当如此——诗歌的审美情趣在大范围内是可以取得一致见解的,这才是诗歌创作的正当的趋附,是主流,也才可能富有当代特色和时代气息。(二)诗歌是建立于形象艺术之上的特殊的审美的意识形态,它对亦有能动的反作用的一面。其内在的要求,就是促发诗人群体内部的解构、分流和重组,并在大范围内达到类似的甚至是共同的代表着主流文化发展方向的审美要求。这是积极的,也充分体现诗歌独特的秉性,这也就说明了诗歌可以经久不息的原因、可以一再地在低谷上迅速地崛起的原因。然而很遗憾,很多诗人们,甚至是颇有见地的文艺理论家因总体认识不够而往往片面地予以肢解。上边的诸多文艺现象不是顶有趣的么?诚然如斯!但仅仅指出现象似乎不足以说明大的问题,是不够的,而惟有挖掘遁形于现象内部的实质才是我们最终的目的。但于此——我却不愿多说,我只提出一些表面的问题:比如上边的现象背后的实质内容,可以作为评判诗人作为,即所取得的创作实绩的一个标准;比如可以解释当今诗坛上流派与宣言多于、大过于诗人圈子的反常现象,亦可解释那些诗人群体们普遍的平平的创作业绩直接的本质的根源。不但缺乏理性的指引,还缺乏诗歌应有的基本的素养,使得很多流派的诗人先生们幻想“惟我独尊”、阴谋“打倒与摧毁一切”,而希图以胜利者的姿态接过诗歌的旗帜,这是很可笑也很肤浅的。是的,他们欠缺包容性,欠缺整体意识,更欠缺积极融入并为营造一个大一统的可以代表主流意识的更合理的审美形态而携手努力的开放者和进取者的现代菁英所应有的雍容的风范和气度,相反各自为营,相互叫骂,于吵吵闹闹中日益磨灭诗歌的本性和创作规律——这是不难理解的。
在序言中我搀杂了不少文艺观点,而似乎使整篇结构松散了,并且不足于表现我的主题“旋转于城市的喧嚣中:世俗的色相”,不知能否得到作者,我的朋友夜白——但愿他如意——以及广大读者的理解,尽管我也有理由相信我的文艺观点较好地融入到主题中去了而了无痕迹。但是到了这我实在有些彷徨了——甚至始于真正开始着手写作时——比如我们出诗集的目的、比如每本集子附带上序言的目的。我能说什么好呢,我又能说什么好呢?其实我的朋友夜白也有着这样的迷惘。商业化的加剧一再把文学推到一切文化的边缘,使得文学成了似乎只有有钱人才玩得起的消遣(这自然是片面的,但却不无道理),比如出一本集子,是要自己出钱的。但不管怎么说,请容许我这样作个不成熟的终结吧:诗人们不殚心力地写诗、出书,是出于对读者的热诚;而我们所作的序言,仅仅为表示对诗人的祝贺和一片崇敬之情!于此,我的朋友,夜白,再度为你诗集的诞生而祝贺罢。
>相关报道:
- ·别江书法作品{苏轼诗一首}[2022-03-07]
- ·素心若兰[2022-03-07]
- ·别江喜迎冬奥书法作品[2022-03-07]
- ·蘇轼诗一首[2022-03-07]
- ·虎跃龙腾[2022-03-07]
- ·别江书法{庆祝第二个警察节}[2021-12-30]
热点新闻
艺术家推荐
更多...曹辉 1952年生于成都。中国美术家协会会员,国家一级美术师,四川美术家协会理事、四川美术家协会中国画艺委会人物画专委会特邀委员、成都中国画会副会长、成都大学中国东盟艺术学院客座教授,硕士生校外导师,成都惠民职工画院顾问。上世纪八、九十年代,其连环画作品多次获得全国大奖。1999年国画《川妹子出川图》获文化部全国第八届“群星奖”银奖;1990~1998年连续在法国举办五次个人作品展。2011年获第一届四川省工笔画学会作品展暨中国工笔画名家邀请展银奖。2014年作品《锦江花月夜》参加四川省诗书画院三十年创作成果展•全国书画名家作品邀请展。2015年作品参加在中国国家画院美术馆举行的“新中国美术家系列·四川省国画作品展”;2016年在四川美术馆举办个人作品展;2016年12月作品受邀参加“回望东坡“2016四川中国书画创作学术邀请展;2017年3月作品受邀参加水墨四川 ——名家作品邀请展;2017年5月作品《锦官城外》受邀参见“守墨鼎新”四川省政协书画研究院作品展;2017年8月作品《年夜饭》参加在香港会议展览中心举办的全球水墨画大展;2018年1月27日在香港云峰画苑总部举行“昔日情怀--曹辉艺术作品展”,并由此开始为期一年的全国巡展。 曹辉1982——2002年发表作品: 《神奇的武夷山悬棺》连环画《奥秘》画报 1982年4期 《给上帝的一封信》连环画《连环画报》 1983年3期 《神秘的大旋涡》连环画《奥秘》画报 1983年2期 《野人之谜新探索》连环画《奥秘》画报 1984年1期 《女子足球运动》连环画《奥秘》画报 1985年5期 《女子马拉松》连环画《奥秘》画报 1985年2期 《小酒桶》连环画《连环画报》 1984年3期 《神秘的石室》连环画《奥秘》画报 1984年4期 《战神之墙》连环画《奥秘》画报 1985年9期 《笔录奇观》连环画《奥秘》画报 1985年11期 《古代美容》连环画《奥秘》画报 1986年6期 《一个女研究生的堕落》连环画广东《法制画报》 85年1、2期 《一个投案者的自述》连环画广东《法制画报》 85年17期 《ET外星人》连环画《奥秘》画报 85年4、5期 《孟卖大爆炸》连环画《奥秘》画报 1987年5期 《热爱生命》连环画《奥秘》画报 1989年1期 《驼峰上的爱》连环画《奥秘》画报 1989年9期 《青鱼》连环画《连环画报》 1985年3期 《珍珠》连环画《连环画报》 1986年3期 《菩萨的汇款》连环画《连环画报》 1985年9期 《小耗子》连环画《连环画报》 1986年10期 《水手长接替我》连环画《中国连环画》 1986年10期 《征服死亡的人》连环画《中国连环画》 1987年6期 《小酒桶》 连环画中国农村读物出版社再版 1985年11版 《给上帝的一封信》 连环画中国连环画出版社再版 84年3期 《日本国技.相扑》 连环画《奥秘》画报 1986年1期 《圣地亚哥刑场》 连环画《奥秘》画报 1987年10期 《古诗意画》 国画 四川美术出版社 1987年5版 《人蚊之战》 连环画 科学文艺 1988年1期 《跳水 》 连环画 《万花筒画报》 1988年2期 《他们与“森林野人”》连环画《奥秘》画报 1988年3期 《圣地亚哥刑场》 选刊 《中国连环画艺术》 1988年3版 《关于圣地亚哥刑场的通信》 论文 《中国连环画艺术》 1988年3版 《阿拉斯加的奇遇》 连环画《奥秘》画报 1989年1期 《祭火》 连环画 《中国连环画艺术》 1989年6版 《辟古奇谭》 连环画《奥秘》画报 1989年6期 《玛丘皮丘》连环画《奥秘》画报 1989年9期 《医生.夫人.闹钟》连环画《奥秘》画报 1990年1期 《南.马特尔之谜》连环画《奥秘》画报 1990年10期 《泉神娶妻》连环画《奥秘》画报 1991年1期 《中国民族民俗故事》 连环画明天出版社出版 1991年1版 《船儿水上飘》 国画 蓉城翰墨 1991年12版 《萨克奇野人的俘虏》连环画《奥秘》画报 1991年10期 《圣经的故事》 连环画四川美术出版社 1992年1版 《雪莲洞探秘》连环画《奥秘》画报 1992年2期 《艾科沟之谜》连环画《奥秘》画报 1992年5期 《印度河文明之谜》连环画《奥秘》画报 1993年1期 《干冰杀人案》连环画《奥秘》画报 1993年5期 《白色幽灵》 连环画 《中国连环画》 1993年4期 《悬棺之谜新解》连环画《奥秘》画报 1993年8期 《冤家变亲家》连环画《连环画报》 1993年10期 《一棵遗落在荒原的种子》连环画《连环画报》 1994年6期 《世界名人传记.艺术家卷 米勒篇 》 连环画浙江少儿社 94年一版 《巴仑克之谜》连环画《奥秘》画报 1994年10期 《辟古奇尼》连环画《奥秘》画报 1995年5期 《豹狼的日子》 上、下连环画 中国连环画出版社 1992年10版 《冬之门 》连环画《中国连环画》 1995年8,9期 《神农架野人今安在》连环画《奥秘》画报 1997年1期 《寻觅玛雅古城》连环画《奥秘》画报 1997年10期 《白鹤梁探秘》连环画《奥秘》画报 1998年1期 《尊严》连环画《中国连环画》 1998年2期 《神秘的南美大隧道》连环画《奥秘》画报 1999年2期 《名医入地彀》连环画《连环画报》 1999年6期 《神秘的英国巨石圈》连环画《奥秘》画报 1999年5期 《蜀王陵出土记》 连环画《奥秘》画报 2000年8期 《定数》连环画《连环画报》 2000年10期 《印山大墓揭秘》连环画《奥秘》画报 2001年5期 《冰封印加之谜》连环画《奥秘》画报 2001年8期 《“狼人”之谜》连环画《奥秘》画报 2002年1期 《扣开通往远古的大门》连环画《奥秘》画报 2002年4期 曹辉艺术年表: 2020年1月在成都举办“陌上谁人依旧 · 曹辉民国风人物画展” 2019年11月作品受邀参加四川省诗书画院主办的“回望东坡•2019四川中国书画学术邀请展” 2019年8月中山(南区)云峰画苑于举办《昔日情怀-曹辉艺术作品展》 2018年10月作品受邀参见“天府百年美术文献展” 2018年1月27日在香港云峰画苑总部举行“昔日情怀--曹辉艺术作品展” 2017年8月作品《年夜饭》参加在香港会议展览中心举办的全球水墨画大展 2017年5月作品《锦官城外》受邀参见“守墨鼎新”四川省政协书画研究院作品展 2017年3月作品受邀参加水墨四川 ——名家作品邀请展 2016年12月作品受邀参加“回望东坡“2016四川中国书画创作学术邀请展 2016年6月 在四川美术馆举办个人作品展 2016年5月 作品《绣娘》参加成都重大题材美术创作工程开篇之作——南方丝绸之路美术作品展 2015年11月 作品《故园旧梦》入选第二届“四川文华奖”美术书法展,并获三等奖 2015年11月 作品参加由四川省艺术研究院主办的“2015四川中国画创作学术邀请展” 2015年10月 作品《西厢待月》参加在重庆举办的“中国精神•民族魂——中国知名画派邀请展” 2015年10月 作品《故园旧梦》参加“从解放碑到宽巷子”2015成渝美术双百名家双城展 2015年9月 作品参加成都市推广天府画派办公室主办的“传神写照•2015水墨人物画邀请展” 2015年8月 特邀参加成都市推广天府画派办公室主办的“心里画儿•中国画邀请展” 2015年5月 特邀参加由四川省美协和四川省美协中国画艺委会联合主办的“四川省中国画人物画作品展” 2015年4月 参加在中国国家画院美术馆举办的“新中国美术家系列•四川省国画作品展” 2014年 作品《锦江花月夜》参加四川省诗书画院三十年创作成果展•全国书画名家作品邀请展 2014年7月 三幅作品参加“南方丝绸之路”主题创作展 2011年5月 在成都东方绘画艺术院(现在的二酉山房)举办“曹辉人物画作品展” 2011年3月 《曹家大院•家训》获首届四川工笔画学会作品展暨中国工笔画名家邀请展银奖 1999年 国画《川妹子出川图》获文化部全国第八届“群星奖”银奖 1999年 连环画《名医入彀》获《连环画报》“十佳”优秀绘画奖 1998年8月 在法国圣雷米市BAYOL画廊举办第五次个展 1996年 作品《寻找北斗》获四川省优秀作品奖 1995年7月 在法国圣雷米市BAYOL画廊举办第四次个展 1993年9月 在巴黎“中国之家”画廊举办第三次个展 1993年 连环画《白色幽灵》获《中国连环画》“十佳”作品奖 1991年5月 在巴黎亚洲民俗艺术博物馆举办第二次个展 1990年3月 在巴黎亚洲民俗艺术博物馆举办第一次个展 1990年 连环画《圣地亚哥刑场》获《奥秘》画报1985~1990年“十佳”优秀作品奖 1989年 连环画《圣经的故事》《青鱼》入选第七届全国美展,获四川省优秀作品奖 1986年 连环画《罗瑞卿的青少年时代》获第三届全国连环画评奖三等奖 1981年 国画《新户头》获四川省优秀作品奖详情>>



 保存
保存 打印
打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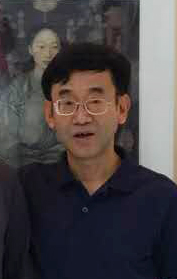
最新评论
已有0条评论,共0人参与